2024 年 9 月,一场连绵大半个月的阴雨让陆续进入榨季的宁夏葡萄酒产区遭遇了始料未及的一击。各酒庄或多或少都受了影响 ——

9 月 24 日,宁夏迦南美地的庄主王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这个榨季的朋友圈比起以往显得太安静了,但是一点也不平静......雨水、烂果、劳工缺乏,绞尽脑汁的酿酒师,但笑容依然还是要灿烂,还是要感恩,抱抱自己。」
同一天,宁夏夏桐酒庄的庄主苏龙也在朋友圈中写道:「认真地看了一下午葡萄园,今年是极其挑战的年份,在葡萄成熟的季节,看到了因为太多降雨导致的叶片霜霉病、果穗灰霉病为主的交织在一起的各种真菌病害。外加市场不景气,果农今年会有很大损失,应该引起重视。图片是看了一天最让我感动、兴奋和学习的葡萄园,在『厂字形』架式大行其道的当下,我看到了传统『龙干形』在创新和工匠精神管理下的潜力。所以说没有架形好坏,有了躬身前行的工匠精神,什么样的架式都能培育出蕴含风土的果实!一个产区,只有当真正优质的葡萄园达到一定比例的那天,才会真正发展好!」

而早在一周前,贺兰晴雪的庄主及酿酒师张静就在感叹:「雨水多,病害多,葡萄真死给你看了。」
迫在眉睫却无能为力,我们亲眼见证了酿酒人的情绪跌宕起伏,焦虑、苦涩、犹豫不决、伤感、沉重、不信邪、遗憾、无奈、苦中作乐,从悲痛到接受,再到寻求解题思路,土地上的人永远比行业其他人更坚韧乐观。葡萄酒行业的本质是农业,但对自然而言,这并非灾害,而是再正常不过的气候变化。土地没有情绪与价值偏向,但人身在其中,总得做点什么。
9 月 28 日,我们前往宁夏,记录下 2024 年这个宁夏葡萄酒的小年。出发前,王方说,快来吧,这可能是你遇到的唯一一个宁夏产区可以休息的国庆节。

「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选择采还是不采?」
没有丝毫迟疑,宁夏迦南美地的庄主王方几乎脱口而出,「采!」
王方记不清,雨是在哪一天下起来的。在她印象中,整个 9 月,天空连日阴沉。每天清晨拉开窗帘,外面就在淅淅沥沥落雨。有时雷雨,有时小到中雨,断断续续,无所谓开始,也望不到尽头。随之而来的是,空气湿度居高不下,「衣服晾了好几天都不干,瓜子拿出来半天就皮了。」身为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几十年间,王方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天气,她称之为「沙漠黄梅天」。

葡萄地里杂草疯长,田间湿滑难行。霜霉菌随着雨水侵入气孔,葡萄叶片由绿转黄,背面爬满白色霜状的斑点。果粒不断吸水涨大,然后在某个节点,随着啪啦一声,表皮破裂,灰葡萄孢菌以几乎肉眼可见的速度繁殖蔓延。第一天 10%,第二天 30%,第三天 80%,直至整串、整块地、整片园子都被灰白色的丝状体侵占。
上个月还并非如此。整个夏天,宁夏虽偶有大降雨,但多属于突发性降雨,一天或几小时内便雨过天晴。那时,王方还抱着丰年的期待。葡萄酒业向来遵循着这样一条自然规律:一个大年之后必然跟着小年,两三个小年之后又会是个大年。从 2020 年开始,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连续几年遭遇极端霜冻天气,今年好不容易躲过霜冻,前期气候、各项数据指标都一片向好,王方和一众同行都觉得,今年怎么着也该是个大年了。「结果还真是个大年,大到所有人直接都懵了。」王方苦笑道。

往年,每逢榨季,王方的朋友圈都是一片丰收热闹的景象。「大家都在晒葡萄、晒酿造、晒加班、晒好吃的,今年太安静了。」所有人都默默盯着手机,从早到晚刷天气预报,看哪天不下雨,能不能逮着个窗口期把葡萄收了。
潮湿,黏腻,宁夏变得不像宁夏,很多以往建立在干燥气候基础上的认知和经验被打破。王方说,往年我们总把 「再放个几天」「再放上一两周」「等一等」挂在嘴边,今年通通失效。葡萄的变化不再以周为单位,从两三天前的葡萄和两三天后完全不同,发展到头一天和第二天不一样,最后发现上午和下午也有差别。「可能你上午刚去地里看过,到了下午就不作数了,变化越来越快,到最后都是以小时来计。」王方以迦南美地协约葡萄园的一块西拉为例,中秋节前她刚去看过,葡萄看起来还很健康,两天之后,她接到电话通知,已经完全不行,甚至无法挽救。自 2021 年起,王方一直用这块地的西拉来酿造 「老王」—— 这是她为祝贺宁夏葡萄酒产业先驱、父亲王奉玉 80 岁寿辰酿的一款单一品种的西拉。「今年『老王』绝产了。」王方说。

据宁夏气象台数据,这场连续性的阴雨天气自 8 月 24 日开始,一直持续至 9 月 20 日结束,总计 28 天。中途除偶尔一两晴日外,基本每天都有降雨。9 月降雨尤其频繁。仅上半个月,银川降雨量就已达到 95.9 毫米,相当于历史同期整月降雨量的近 4 倍,也几乎占据了年均降雨量(200 毫米)的一半份额。
连阴雨的影响,不仅在降雨导致的真菌感染,还有光照不足带来的葡萄成熟度不够、糖分普遍上不来的问题。独立酿酒师、迦南美地酿酒顾问周淑珍表示,从业 40 多年,没见过宁夏还有这么低的糖。据她介绍,赤霞珠的含糖量以 240~250 克最为理想。往年,宁夏不少酒庄赤霞珠的含糖量能达到 260~270 克,今年很少有超过 230 克的。「往年是『糖太高,愁死了』,今年变成了,『糖怎么还不上来,也愁死了』。」8 月 20 日,周淑珍在北边的金山地块查看,还在为 257 克的糖分发愁:(采收)还早着呢,现在就飙这么高,这酒咋做。没成想,连续几个阴雨天,葡萄里的含糖量开始直线下降,「先是降了 9 克,下一次测又降了 6 克,一次比一次低。」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不仅糖在降,酸也在降,整个果实都被稀释了。

在葡萄酒酿造里,采收时间直接关系着一款酒的酒体与风味。采收过早,果实成熟度不够,糖分和酒精度上不来,一旦错过最佳采收时间,果实又很快失去支撑酒体的酸度。为了理想的糖酸比以及风味物质的积累,一些酒庄选择耐心等待雨停。王方为保险起见,选择先采收一部分,然后再加入「等待大军」。「当时我还不信邪,因为宁夏从不会连续下几个礼拜的雨,我当时想,顶多下一个礼拜就停了。」另一方面,她对自家葡萄园的前期防病管理很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紧迫起来」。
形势是在中秋节后急转直下的。9 月 17 日中秋节,是宁夏难得的一个晴天。当地气象局预报接下来还有雨,不少酒庄都抢着这个空档采收。周淑珍打来电话时,王方正陪家里人吃饭,「过节呢,着啥急。」她有意再等一等。结果不出意外地,隔天又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今年的天气预报真是一点没让我失望,准得一塌糊涂。」王方好气又好笑道。

从那天开始,王方的心态就变了。只要不下雨,拖拉机进得去地里,能采的都开始采。比起「采收」,她觉得更贴合今年榨季的说法是「抢收」,和老天抢时间,和同行抢人手。「今年劳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方说,晴天一共就那么几天,所有酒庄纷纷扎堆采收,人手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全区农作物受损,这些日子,地里的玉米、马铃薯、大枣和枸杞陆续都在抢收。前几日,王方见果皮渣还堆在那里未处理,一问才知,工人回家收玉米了。「往年我们还有志愿者,还外头雇人,今年雇人特别难,全是自己来。」王方也加入了下地干活的行列。
随着榨季进入尾声,雇工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往年,采摘工都是按筐计价,降雨导致采收难度普遍增大,这种结算方式很难再招到工人。「今年我们都是按小时算,跟工人说好,你只管剪好葡萄,坏的留下来,算下来今年采收成本相当于往年的两倍。」即便如此,迦南美地还是有一块地没来得及采收。那是酒庄最东边的一块雷司令,王方特意留着没采,她原本打算今年试水德国著名的 Sp?tlese(晚采雷司令)。「在宁夏做晚采不太可能,尤其雷司令这种容易染病的娇贵品种,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总期待着一点意料外的惊喜。」

王方事后复盘,如果当时连日连夜地采也能采完。她记得那期间有半天天晴,工作人员问她要不要采,她反问,能采吗?对方回答,反正凑合着也能。王方说,那就先不要管它。「当时一方面是好奇,想说留一块地放着,看它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二来还是不相信,这雨真的能下那么久。」周淑珍提醒她,继续放下去的风险可能是下完雨葡萄就没了,王方表示接受。「当时还是抱了侥幸心理,想着只要扛过去,没准今年就能做出来一个晚采。」现实给王方上了实打实的一课。「大概有 7 吨多的雷司令没有收上来,」她顿了顿,接着说,「有时闭上眼睛,我还会在想,当时要把它抢了回来,还能有三四吨的酒。」
9 月 28 日下午 4 点,最后一筐赤霞珠入罐后,迦南美地上下都松了口气。大家凑在一起聚餐聊天,王方没加入,她上楼洗了个澡,脑海里开始盘算后续酿造的事。「葡萄酒就是前期的葡萄园和后期的酿造车间,」她说,「前面的仗我们手忙脚乱地打完了,其实真正的战役还在后头,接下来才是酿酒师变魔法的时候。」魔法曾生效过一次。2018 年,同样因降雨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温,葡萄受灾严重。但王方和酿造团队依然做出了迦南美地最高端的「魔方」,「尽管量很少,但我们只要能做出来,能在艰难年份里做出好酒,这说明我们团队整体都通过了考验。」
这一次,酿酒师的魔法还会继续生效吗?王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她的视线转向外面的客厅。那里沿墙立着一幅她从德国带回来的金色埃及女神画像,角落里有一行蝇头小字。王方引了那行小字:Ich habe das Gestern gesehen,ich kenne das Morgen.(我看到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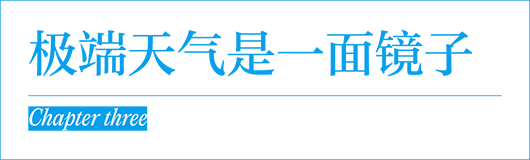
自 2005 年建庄以来,今年是贺兰晴雪第二个 8 月就开始采收的年份。据酿酒师张静介绍,一般情况下,贺兰晴雪的采收是 9 月 10 日前后,由白葡萄霞多丽拉开序幕。2023 年,提前到了 8 月 29 日。今年,则又比去年整整早了一周。8 月 23 日清晨,工人便来到酒庄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开始采收早熟的霞多丽。
回头来看,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8 月 24 日就开始下雨了,我们是雨前最后一天采的,霞多丽基本没有受影响。」张静听说有些酒庄是这场雨后采收,白葡萄多多少少有些染病。「所以说今年一丁点都不能犹豫,越是犹豫越是损失。」但她到底还是没躲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连阴雨。8 月 30 日采收黑比诺时,张静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那时候就感觉到空气湿度很高了,但你已经来不及再做出干预。」张静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到叶幕通风管理上。丰沛降雨过后,地里的马齿苋等行间草疯长,「刚开始还都是趴在地上,后面噌一下能长到小腿那么高」,大大影响了葡萄田的通风条件。

焦虑的情绪便从那时生发。9 月 18 日采收马尔贝克时,张静的焦虑值达到了顶峰。那是她引以为傲的一个葡萄品种,以此酿造的马尔贝克干红曾摘得中国马尔贝克最高荣誉。这场连阴雨尚未抵达前,张静和种植师牛文奇去地里察看,两人都相当满意。「往年果粒比较大,今年我们水肥控得特别好,大小很匀称。」张静记得,自己当时还特别表扬了一番小牛。
一切发生在 10 天内。从长势喜人到涨大破裂,最终覆水难收。「你知道它最后变多大了吗?」张静拇指和食指合拢,摆出了一个汤圆大小的圆圈,「我不夸张,就这么大,就跟鲜食的(葡萄)一样。」马尔贝克都涨这么大,其他葡萄肯定也都稀释了,张静当下断定,继续等待已无意义。而且她也发现,即使不下雨,光照不足,葡萄留在地里,糖酸等风味物质也不会继续累积。相反,一旦遇上雨天,糖酸还会继续走低。

20 年一线葡萄园管理与酿造经验告诉张静,但凡犹豫不决,事情会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今年就不要求糖度了,健康的葡萄是第一位的,只要晴天就赶紧采。」从那天起,酒庄上下 20 余人,人人便如同一张拉满了弦的弓,时刻准备着采收。9 月 20 日,美乐。22 日,品丽珠。23 日,马瑟兰。一直到 27 日,最后一块地的赤霞珠采收完成。
从 9 月 18 日到 27 日,除了友情转发一条民宿开业消息,张静没再发过一条朋友圈。「根本没空,每天忙得要死。」那 10 天,她没回过家,吃住都在酒庄。每天上午 8 点到晚上 11 点,除开午休一会,她几乎 12 小时不间断地守在分拣台上。张静解释称,在葡萄田里不一定能看到葡萄全貌,但在分拣台上,相当于每一串葡萄都经过了你的手与眼,健康还是不健康,不健康的都有哪些表现,有没有其他品种混进来,全部一目了然。严格分拣,是她对自己和团队的一贯要求。往年,她都会亲自把关这一环节,今年更不敢掉以轻心。

「今年的葡萄病害多是复合型的,灰霉、霜霉之外,还有酸腐。有些葡萄在树上看着还好好的,手一碰,果皮直接就分离掉了。还有的一串果穗里发现一粒生病的,以为摘掉就行,结果摘完发现里面也都感染了。」张静明白,在整体葡萄原料不如丰年的前提下,风味上想要追平甚至超越,就必须把分拣做得细一点,再细一点。
葡萄采收时,第一遍粗放的分拣已经开始。种植师牛文奇实地监工,要求采摘工只采健康的葡萄。到了分拣台,再开始串选。「今年串选工作特别难,有些生病的果粒从筐里倒在分拣台上时就自动掉下来了,我们除了剪串外,还要一捧捧往外捡这些脱落的坏果。」串选之后还有最后一轮的粒选。工人们围着一个不断震动的粒选台,一颗颗果粒,来来回回筛。针对运送葡萄的塑料筐,张静也要求员工,当天用过的必须用高压水枪清洗干净,哪怕几小时后还要接着使用。「可能有人不觉得有什么,但这些工作是必须做的,今年尤其。」张静说。

产量大幅度降低是严苛分拣的最直观结果。以马瑟兰为例,采收量不到 3 吨,分拣台上被挑掉一半,最后真正入罐的仅剩 1.5 吨。「今年用挑剩葡萄蒸馏的杂酒,要远远多于正式的酒,别看这些(发酵)罐都是满满的,其实那些 10 吨的大罐里都是杂酒,正式的酒都是 2.5 吨、5 吨的小罐。」她笑着打趣,话语间却尽是苦涩。苦涩之外,还有一层深深的遗憾。在张静的酿造计划里,她原本打算今年做一款轻盈的马瑟兰,类似于法国南部的风格,清新、活泼,果味新鲜。雨水以及随之而来的病害,将这一实验性的探索扼杀在摇篮里。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张静形容,极端天气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酒庄很多薄弱的环节,尤其在葡萄园的栽培管理上,还需要学习和进步。
她有一个「两个月」理论:一年收成如何,并不取决于你当下做了什么,而是两个月前你在地里做了什么。「如果你两个月前的工作做到位了,即使遇到极端天气,也不会出现今年这样的状况。」她以自家的一块葡萄田举例。那是位于酒庄入口处的一块长方形葡萄地,前面种着美乐,后面是赤霞珠。还在生长期时,张静安排工人给葡萄树喷石硫合剂(在农业和园艺中,石硫合剂作为喷雾剂以预防真菌、细菌和昆虫,在欧盟和英国被批准用于有机作物,会在采收一个月前使用),喷到赤霞珠地块的一半,机器坏了,还剩下几行。修好后打算继续,迎头赶上降雨,就这么一再耽搁。此刻,站在葡萄园高处眺望,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分界线以东是没来得及干预的葡萄藤,病斑连成一片,以西是喷过药的,枝叶郁郁葱葱,呈现一种生机的绿。

9 月 28 日,最后一筐赤霞珠入罐后,张静粗略估算,今年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 1/3。「其实后期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两个月前的工作也都做了,只是没有做到位,才造成了今年这么大的损失。」客观说来,整个产区范围内,贺兰晴雪的反应相当及时。一意识到降雨严重性,张静早早便开始了应对之策:给田间除草,增加通风;发现烂果及时清理;果断开始采收,避免了感染蔓延。张静总结,说到底,还是重视度和反应速度不够快,应对阴雨天气的经验不足。个体层面,她认可今年是一个全面学习和成长的年份。「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极端天气,就可以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
除此之外,这场灾害也带来了一些认知上的新发现,比如她了解了在湿度特别高的时候,国外某些葡萄园会使用一种鼓风机,对着葡萄地吹风,以此增加通风。她还发现,北玫、北醇等原产于中国的红葡萄品种在今年的极端天气下表现很好,几乎没有病变。「在葡萄酒的世界里,你知道的越多,就意味着你知道的越少,」张静说,「这就好比你画一个圆,你知道得越多,意味着圆的直径越大,圆的面积越大,但同时圆圈 touch(触及)的外部未知领域也就越多。」这让她心生敬畏。

十多年过去,张静一直记得第一次在国内米其林餐厅见到加贝兰时的雀跃,那种油然而生的骄傲。在她的观念里,于一位酿酒师而言,敬畏与骄傲是同等重要的滋养。它们也许无法被语言精准捕捉,但正是这种无限接近于精神性的东西,支撑并引领着一代代宁夏葡萄酒人风雨同舟,前赴后继,将这一产区带到了世界舞台上。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张静认为,这种极端天气也是给蒸蒸日上的宁夏产区的一记提醒。宁夏因气候干燥,过往少受霉病的侵扰,常年下来,导致从业者对栽培这一块重视不够,无论技术引进还是人才配比,对栽培的投入都要远远低于酿造。她以人才队伍举例,整个产区有很多从顶尖学府学成归来的酿酒师、酿酒顾问,但要找出一个知名的葡萄栽培师简直凤毛麟角。但葡萄又是最重要的,好葡萄是一切的基石,张静说,一位糟糕的酿酒师可能会把完美的葡萄做得一塌糊涂,但再伟大的酿酒师也不可能把一堆烂葡萄做成伟大的酒。

关于葡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酒的风味,夏桐酒庄总经理苏龙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表述:「请你们记住,你们只能表达质量,不能创造质量。」这是他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学习酿酒时,导师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今年,苏龙被同行一致调侃为宁夏葡萄酒圈里「最幸福的人」。他微笑认领了这一称号。夏桐酿造起泡酒,1000 多亩的葡萄园主要种植早熟的霞多丽和黑比诺。7 月 30 日,在大多数赤霞珠还处在转色期时,夏桐便开始了今年的采收,并未受到那场连阴雨的影响。但相比大多数同行,苏龙更早察觉到了雨水的威胁。8 月 8 日,银川突降一场强暴雨,「很多地方一天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局部下了 200 毫米。」幸运的是,夏桐所在区域降雨量只有 10 毫米。「如果 100 毫米在我们那下了,我们那点黑比诺也都没有了。」

「今年是老天爷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它并不会一直优待你,所以不管雨下不下,根据它的生物规律,你该做的植保就要做,该防的病就要防。」苏龙说,宁夏产区因长期处于干旱状态,一般正常年份葡萄不会得病,这也导致了从业者葡萄园植物保护意识不强,对于喷药管理,叶幕的通风透光等也未形成一套科学认知。他带我们走访了青铜峡产区两块相邻的葡萄田,同样的石子地与风口的微气候,同样遭遇连天的阴雨,一侧病虫害症状明显,望过去一片青黄颓败之象,另一侧藤蔓遒劲,果穗稀疏,果粒表皮一层薄薄的白色果粉 —— 那是葡萄健康的标志。

这片葡萄田的主人是有数十年葡萄栽培与种植经验的陈雄。和多数人一样,他虽不相信这场雨会持续如此之久,但还是防患于未然,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给 1220 亩的葡萄田喷洒了波尔多液(一种杀真菌剂,常用于葡萄园、果园和花园,以防止霜霉病、白粉病和其他真菌的侵扰,因在波尔多地区首先使用而得名)。
另一方面,不同于如今大行其道的「厂字形」架式,这块葡萄田维持着传统的龙干型。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架式结构,如其名,一支主干两边长出新梢,梢上挂果,就像龙骨两旁的肋骨一样,枝蔓整齐,方便北方冬天埋土。在今年极端的降雨天气里,左右两边水平延展的枝叶藤蔓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像伞一样,雨水落在叶片上哗一下就滑走了,不会影响到下面的果穗。」

这也启发了苏龙关于葡萄种植与葡萄园管理的更多思考。「这种传统的龙干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值得拿来再去考量。」相关数据显示,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夏的年平均气温已升高超过一度。气温升高导致水循环加快,这也是近十年来宁夏降雨量呈逐渐上升趋势的原因所在。当湿润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片习惯了干旱的土地,如何在变动中建立起新秩序?这是悬在每一位从业者头顶的问题。
榨季已接近尾声,情况大多都不乐观。整个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石嘴山、贺兰、银川、永宁、青铜峡、红寺堡,由北至南,无一幸免。其中,南边的青铜峡因是石头地,又是风口,雨量相对较少,整体情况相对较好。北边的金山地块因雨水多,受灾尤其严重,考虑到葡萄状况和节节攀升的人工费用,个别葡萄园干脆没采。年景不佳,再叠加消费低迷,很多酒庄面临双重困境。

但在公共语境里,这些仿佛从未发生。圈子里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保持缄默,担心造成消费者对宁夏葡萄酒不好的认知;另一种则认为回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发生就讲述。苏龙是立场坚定的后者。「实事求是地讲,今年肯定是糟糕的一年,产量损失、品质不好,但从葡萄酒产业的特点和规律来说,它(困难年份)也是这个产业的一部分,不可能全是好年份,大家不能在做产业的过程中保持『皇帝的新装』这么一个状态。」在苏龙看来,一个葡萄酒产区的建立与背书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味重复「好」是相当平面的,但一个产区如何应对「不好」,则是更立体动人的故事。他打了个比方,如果将来要做一个 10 年的垂直品鉴,那么今年很有可能是会是被浓墨重彩讲述的一年。
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苏龙发现,有些葡萄园连基础的农业保险都没买。让声音传达出去,也许能让相关主管部门有所关注,对受灾严重的葡萄园给予相应救助或扶持。夏桐总经理一职外,苏龙的另一身份是银川市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联盟理事长。他习惯用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在他的观念里,产区与葡萄酒的故事,最终还是要回到土地和葡萄园。故事都是飘在天上的风筝,土地与葡萄园才是那根牵着风筝的线。它是产区真正能和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的部分,也是区别于波尔多等国际产区的部分,用他的话说,现在很容易就能买到波尔多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名庄的酒,但老百姓要去到葡萄园和酒庄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每年,除自己的葡萄园外,夏桐也会从酒庄的合作伙伴处择优收购部分红葡萄。眼见今年这一现状,酿酒团队不建议外收葡萄,但他还是坚持收购了部分。「我还是想看看这个年份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在苏龙看来,葡萄酒的迷人恰在于它每个年份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做出来的每一个年份、每一瓶葡萄酒都像可口可乐那样标准,还有什么意义?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它的文化属性,是葡萄酒多元性的体现,也是酿造真正迷人之处与魅力所在。」
张静也抱有相同的想法与期待。尽管今年马尔贝克提早采收,成熟度和糖度还不够,但她还是决定继续推出 2024 年份的马尔贝克,「不仅要出,我还要单出一个 2024 年份。」她也不打算采用放血、浓缩等工艺,就还原它本来的样子,酒精度是多少就多少,就看它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年份会有怎样的表现,可能最差的年份,莫过于此了。事情往往在不抱期待中迎来转机。9 月 18 日,2 吨多的马尔贝克入罐打上循环后,张静取样品尝,不似想象中的寡淡,「它的果香很干净,风味也有,比想象中要好很多。」一个新的想法已在她脑海中酝酿成形,她打算将今年的马尔贝克入旧橡木桶,尽量保持它的纯净果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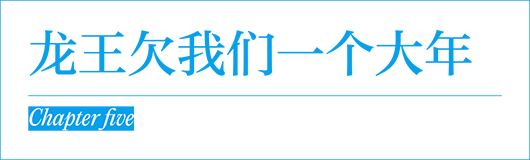
「龙王欠我们一个大年。」在今年的宁夏葡萄酒圈,这是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对于宁夏大大小小近 130 家酒庄而言,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自是不可估量的,但苏龙和张静都认为,绝大多数酒庄都能挺过去,它并不会让一家酒庄走向生死存亡,「除非今年已经是这个酒庄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真正致命性打击的,是处于产业链底端的果农与种植户。9 月底,大多数酒庄榨季已结束,一果农找到张静,给她看自己地里健康的葡萄,问她 3 元一公斤收不收(近些年,宁夏酿酒葡萄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 6~7 元)。那一刻,张静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她清楚地记得,贺兰晴雪刚建庄时,葡萄就卖 3 元一公斤,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桌子为农民鸣不平。20 年过去,又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价格。而这次,即使如此低价,也很难找到买家。「很多果农幸苦了一整年,到头来只能让葡萄烂在地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张静的话语里,带着一种无法回避的伤感与沉重。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果农的担忧。王方说,1 元钱对葡萄酒而言无足轻重,但对果农来说,那是实打实的收入。王方的父亲一直对女儿强调,如果说宁夏葡萄酒产业是一座金字塔,果农就是底下的基石,如果他们挣不上钱,这座金字塔也不会牢靠。相反,如果果农获得了高价的葡萄收入,他们也会更用心细致地关爱地里的葡萄树,如此,一个健康、正向的循环才得以成立。
但面对宁夏葡萄酒产业 40 年间的历史性天灾,没有什么更多现成经验是可以被传授的。一众酿酒人只好互相劝慰着,「今年就当自然降低库存了」,又或者「龙王欠我们一个大年」。

但当我们把视线从葡萄移开,站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上来看,这场连续性降雨对于贺兰山的整体生态环境而言,却是一次巨大的喘息之机。丰沛的雨水使土壤变得松散,空气里少了干燥泛黄的尘埃,湿润的味道令鼻翼轻微颤动,一些平日里难觅踪迹的小动物开始显现。王方注意到,今年酒庄的昆虫前所未有的多。苏龙也听林业局的前同事说,今年贺兰山中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物种。光秃秃的石头山哗啦啦冒出一大片青,嫩绿的新芽纷纷从岩石缝隙间探出头,往年踪迹难觅的马鹿,开始成群结队往山下走。
蝴蝶翅膀扇动的力量是巨大的,若干年后,这场雨水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未尝不会作用于葡萄田的土壤与根系?也许未来某一天,这片被雨水充分浸润过的石头地也会催生出某种别具一格的风味?这听上去仍有某种自我劝慰的意味,但是,谁知道呢。就像这场 28 天的连阴雨真正到来前,没人预知过它的存在。